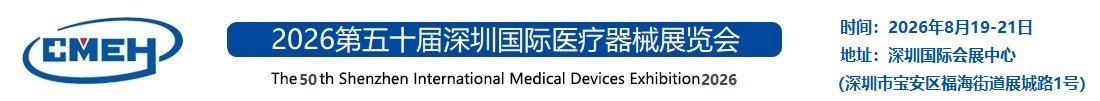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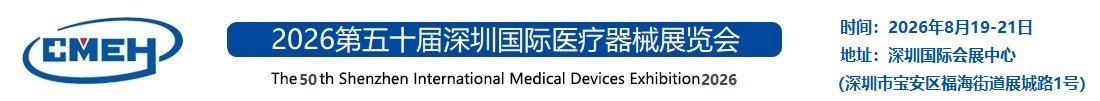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下是否真的全面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马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从中央到地方很快建立了垂直管理的疫情防控体系,可谓举国防控疫情。可以说,不管是国家部委的布局,还是地方政府的防控都有大数据助力“战疫”的身影。
大数据防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掌握人口流动数据,提前布局疫情防控与重点人员定位;二是通过对健康医疗数据分析获得易感人群的数据,实现重点防控。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大数据进行疫情防控的同时,也暴露了部分法律制度的空白与统筹治理的相关问题。
人口流动数据共享打造联防联控
本次疫情的大规模扩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春运期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人口流动数据共享联防联控分为两部分:一是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预防联控;二是疫情人口流动过程中密切接触者隔离防控。
就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预防联控而言,在疫情大范围暴发时最为引人注意的便是浙江杭州针对武汉赴杭州航班乘客信息的利用。
当武汉飞往杭州的飞机确定登机人数时,在购票时输入的购票人信息和登机人信息确认一致时,某航空公司将机上乘客信息共享给杭州航空管理部门。在接到航空公司的报告信息后,航空管理部门将该航班所有乘客数量和乘客身份信息共享给当地政府疫情防控部门。杭州市疫情防控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实行统一部署,完成了从落地统一运送到人员分散共享隔离管控一体化防控,有利于早发现病人,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就疫情人口流动过程中密切接触者隔离防控而言,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一旦发现有人为疫情人口,当地政府都会统一发布官方急寻密切接触者通告,通告中一般会包含确诊病例人员的活动轨迹。
此活动轨迹便是电信运营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600050,股吧)、中国电信、中国广电)根据手机号码调取的确诊病例人员的活动轨迹。调取四大运营商关于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信息,只能由公安部门根据法律授权依法进行,其他政府部门无法获得电信运营商用户的活动轨迹。
当公安部门获得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后,会选择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作为搜集条件,筛选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与确诊病例接触过的密切接触者。寻找完密切接触者之后,公安机关将会把收集到的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向其他疫情防控部门进行共享。其他疫情防空部门获得数据后,将会把相关信息向市辖区或县级疫情防控部门共享该信息,以便区级、县级政府及时与密切接触者进行联系,提前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健康医疗大数据助力重点人群防控
健康医疗大数据适用的前提是特定行政区域内建立对社区居民完整的健康医疗卫生数据集。以银川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助力重点人群疫情防控为例,在我国,银川在互联网+医疗产业领域走在前列,建立了完整的城市社区居民健康卫生信息体系。笔者获悉,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银川市委网信办、市网信局、市大数据产业服务中心,联合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北大医信健康医疗大数据实验室银川中心和汇天下(银川)大数据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易感人群信息,将易感人群信息作为基层社区健康医疗数据的对比条件,形成银川市重点易感数据分布结果。
在将重点易感数据结果形成报告后,通过市政府统一向市辖区、县共享报告,市辖区、县可通过该报告针对易感人群分布进行重点部署,从而通过提前防控重点易感人群来减少疫情的传播。
精准防疫需要做得更好
在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大数据作为新的技术手段部分代替人力,起到了弥补人力所不能及的作用。不管是人口流动数据,还是健康医疗大数据,都是通过数据分析进行提前布局。此次疫情下,数据的共享与流通再次凸显了我国大数据领域立法的空缺,也暴露了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疫情发生后,存在采集公民个人信息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需求,但在网络安全法或其他部门规章中,无法找到一般情况下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解药”。目前,人们仅能从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找到紧急情况下的相关规定。
域外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或许值得借鉴。
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了数据收集主体在收集数据时的6个合法性事由,包括“为公共利益而执行任务,或数据控制者履行赋予的公共职能时”“为保护数据主体重大利益或其他自然人重大利益而必须处理个人数据时”等。
此外,印度2019年《个人信息保护法案》(草案)第12条e款也回应了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在流行病、疾病暴发或其他存在公共卫生威胁期间,为了向任何个人提供医疗或健康服务”可以采集使用相关数据。
其次,在我国,现阶段健康医疗数据的概念存在重合与矛盾,而且概念往往源自于卫健委规章内部。
例如,原国家卫计委《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行)》(国卫规划发〔2014〕24号)第3条认为,“人口健康信息”是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工作职责,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服务机构在服务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人口基本信息、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等人口健康信息。而在官方解读时,又将范围具体化“主要包括全员人口、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以及人口健康统计信息等”。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第4条认为:“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在人们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等过程中产生的与健康医疗相关的数据。”虽然《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与《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这两部规定立法目的不同,但两者所定义的概念实则为同一范畴。
实践中认为,“健康医疗数据”包含的范围应当是最为广泛的,不仅包括人口健康信息、人类遗传资源、病历信息,还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健康管理信息等多种类型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但就目前的相关规定而言,人口健康信息和健康医疗数据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再次,此次疫情防控给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在利用政务数据提升行政效率方面。诸如人口基础数据、交通数据、物流数据等难以实现及时共享,出现了数据“割据”的局面。
2016年,国务院就发布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旨在加快推动政务信息系统互联和公共数据共享,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时至今日,各部门之间的核心政务数据共享仍然困难,实践中也时不时会出现不同业务需要在不同政务服务APP上办理的情况。
综上,虽然大数据在本次“战疫”中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为提高社会治理提供了帮助,但其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下是否真的全面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此外,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此后的大数据建设应当如何推进?
来源:法治周末